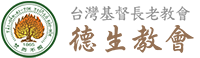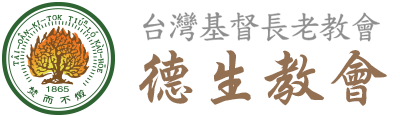我於1923年出生在大溪的郊外,和母親養父母家的親戚共住於一棟獨立的土壁農舍。我家除了大廳之外,左右兩邊各有兩間側房,為臥室和廚房;屋外另蓋一間豬舍,並設有廁所。美其名曰之廁所,事實上是在豬舍糞池上鋪了兩片木板,在那裡方便的。古時候的房子採光奇劣,據說是為了抵禦匪賊,盡量減少窗戶,我家的大廳和外側兩間側房之採光只靠大門。門扇是以厚木板做的,沒有空隙。因此有人在家時始終敞開大門以利採光,而中間側房即隔成臥房及通道,通道壁上只挖了一個小小的窗戶,但臥房是完全密封的,只靠屋頂嵌上一小片玻璃的天窗,整年暗暗的,通風也不順。後來日本政府為了改善民間之生活環境,到處張貼標語說:陽光照入之家,醫生不踏入。鼎力獎勵大家增設窗戶,於是民間的窗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大了。
當時很多住宅是以黏土捏成四方形土塊(台語稱為土角)來建築的。雖然是以黏土為原料硬度不高,但牆壁極厚,倒是很堅固,不過颱風來襲時,父母親常常緊張得不得了,深怕橫掃的狂風豪雨把土壁沖潰吹垮。
我家共有六個人;分別是父母親、大哥,我及兩位養姐妹。當時在台灣,尤其是北部,有一種陋習,就是習慣將自己的親生女兒送給別人作養女,卻抱回別家的女兒當養女,大部分是童養媳,計畫將來把養女許配給自己的親生兒子做媳婦,當時的社會認為將準媳婦自幼抱來教養,會比較適應。
我家也不例外,家母本來是沈家的女兒,卻過繼給張家做養女,再從張家出嫁到林家來。而我大姊出生後不久就送給王家做養女,後來許配給王家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姊夫。而家母抱養了兩位養女,計畫給大哥和我做媳婦,但都不了了之。我妻子的家庭也是一樣,她有五位蔡姓胞姊妹,其中四位即做了別人家的養女。
家父於三歲時喪父,在無祖產的情況下,自幼即靠勞力維生,歷盡辛酸;後來與家母結婚,夫妻恩愛,同甘共苦,建立了一個健全的美滿家庭。家父在深山裡從事伐木工作,雖然辛苦又危險,但其所得較多,家母勤儉持家,並在學校門前擺設文具攤以幫助家計。
家母極重視教育,她本人也上過私塾勤學中文,甚至加入吟詩會與同好文人互相研習作詩。當時的家庭主婦會讀書、寫字、作詩可是一件足以轟動鄉里的奇聞。家母對下一代抱了很大的期望,克服萬難安排我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彰顯了無窮無盡的母愛。
我於八歲時入學大溪公學校(國小),它離我家大約有兩公里的路程,上學時必須步行將近四十分鐘的鄉村小徑。途中是一片曠野及水田,無處可以躲避烈日及風雨。大熱天時是滿身大汗,寒天卻是冷風刺骨,遇到雨天更是路滑難行,求學可說是一件辛苦的事。
當時的學生幾乎都是打赤腳上學,我也不例外;不過我與一般同學一樣擁有一雙布鞋,那是過年及參加學校慶典或親戚喜宴時才穿,平時絕捨不得穿。穿鞋的日子,如果半途遇上下雨,就趕快脫下來抱於胸前,免得它淋濕。
我們出門一概頭戴斗笠,既可防日曬又可躲雨,方便極了。如果是雨天,我們就穿著蓑衣上學,蓑衣是以棕樹的棕鬚編織的,又粗又重,其領口刺痛頸部極不舒服,但卻是當時唯一的擋雨用具。
雖然鄉下學童上下課很辛苦,但卻能體驗到都市兒童得不到的樂趣。我們常常於週末假日相偕去探險,有時去同學家採龍眼或楊桃,有時鑽入叢林裡捉秋蟬,或跑到小溪裡捉魚蝦,無憂無慮的盡情玩耍。
不過有時也得付出代價,我們玩得忘卻一切,等到暮色漸濃,太陽快要下山時才突然驚醒,趕快以全速跑回家。但總是遲了一步,時常驚見母親已經站在門口,一手叉腰,一手拿著鞭子。於是趨前,陪著媚笑說:「媽!我回來了。」但擔心我們安危,已經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母親,在放下心中一塊石頭的同時,怒氣便衝上來了,兩頰鼓得圓圓的,不由分說,抓住我(通常是我和哥哥),舉起鞭子,一下又一下地抽打我們的屁股。
此時,累積了豐富經驗的我,學會了攻心戰術,在鞭子尚未落於屁股之前,就要哀哭著說:「媽!我下次不敢了!」這招是非常管用的,聽到愛兒悽慘哭聲的母親,心軟了氣也消了,如此便可以少挨幾下鞭子。
以前愚蠢的我曾經採取孫子兵法的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母親要追打時,我便拔腿就跑。母親是跑不過我的,可以暫時避免皮肉之苦,但其後果卻更悽慘,因此之後學乖了,才改採哀兵策略。
某一天下午母親到街上去買東西,叫我和哥哥在家寫功課,我們寫完後就相偕跑到鄰居的小池塘玩耍。那口池塘是為蓄存菜園的灌溉用水,但裡面卻藏有許多的寶貝,如田螺、田蛤、水蛙及成群的小魚。
我走到池邊,看到池裡有一條大鯽魚,急著想要捉住它。沒想到身後有一塊石頭,是鄰居挑水時用的踏台。我猛蹲下去的時候,屁股撞到那塊石頭,反彈起來一頭栽進水塘裡去了,這下我們兄弟倆可驚慌了,因為母親怕我們溺水,是嚴禁我們玩水的。
於是我們兄弟想盡辦法來補救,將衣服脫下,一人一端握住衣服,使盡全力,絞乾濕衣,然後在家門前的大石頭上敞開曬太陽。光著身子在烈日下蹲著等候,好像曬我能加速衣服變乾的樣子,並屢屢伸手去摸它。但它一點兒都沒有乾的現象,真是急死我了。
雖然那天是大晴天,刺眼的太陽高掛於中天,但總覺得那天的太陽不爭氣,不夠熱。而另方面覺得那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衣服久久未乾,深怕母親回來後發現我又闖禍;平常母親出門時,巴不得她趕快回來,但那天反而盼望越晚越好!
哥哥一直站在籬笆邊窺探外面,看看母親是否回來了,不一會兒,他忽然大叫媽媽回來了,於是趕緊穿上半乾半濕的衣服,哥哥則用力幫我拉平衣服的縐紋。
母親走到門口,我們若無其事地向她打招呼。但我們的詭計瞞不過母親的慧眼,她伸手摸我的衣服後怒責:你們又不聽話,跑去玩水了。說罷,便揪住我,後來的情形不必我多說,大家應該都可想而知。
事畢,母親的氣消了,恢復以往的慈母像,並給我們一人兩顆糖果,那是剛從街市買回來的,當時一分錢可以買十粒。我將其中一粒塞在哥哥的手裡,表達他對我無所不至之照顧,以及為我挨打的感謝和歉意。像這種童年的許多糗事、樂事一大籮筐,現在回想起來,滋味蠻甜蜜的。
我幼時,大溪的電燈尚未普及,只能在政府機關及富裕家庭中才可以看得到,一般家庭都用煤油燈來照明,很多人不明白電燈的發光原理。某一個晚上,一位肩掛大煙斗的老公公,仰頭凝視路燈感慨的說:時代進步了,這麼細的油管竟能點明那麼亮的油燈(他以為電線是油管,而電燈是燃燒煤油發光的)。
大溪唯一的搗米廠也未採用電動碾米機,而是以水車推動木杵在石臼內搗米。高大的水車置於小溪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停地轉動,蠻富有詩意的。
我第一次聽到留聲機是在國小一年級的時候。那天是上半天課,於中午下課回家途中看到一間銀樓門前圍滿了人潮,我好奇的鑽進前面一看,店裡放置了一台留聲機,老闆上緊發條後把唱片放上去,竟唱出流行歌來了。聽眾的驚嘆聲此起彼落,議論紛紛,有人說那是魔術,也有人說如何把人藏到這麼小的盒子。老闆看大家的興趣未減,乾脆連中午也不休息,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播放僅有的兩張唱片,讓大家欣賞。來聽的人爭相傳報親友,以致一波又一波的人潮長久不退,而我竟然也達忘我的境界,忘掉肚子餓,甚至忘掉回家,癡癡的站了一個多鐘頭,回家後被母親痛罵一頓。
我頭一次收聽電台的廣播是在國小二年級的時候。在這之前我的同學中沒有人看過收音機。校方為了讓學生見識見識收音機,特地舉辦了一場試聽會,將全校的師生召集於操場,遠從桃園聘請專家攜帶收音機來主持。開始之前老師先講解,電波能經由空中把聲音傳送到很遠的地方,如今我們要聽的聲音是從台北播出,並宣揚現代科學之進步。開始後,收聽的作業一直不順調,只聽到嗶嗶喳喳的雜音,根本收不到廣播。那位專家弄了很久,始從收音機中傳出一兩句談話聲,隨即又故障了,爾後怎麼弄也弄不出聲音,於是宣布散會。
雖然我們枯坐草坪半個小時只聽到兩句話,但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互相津津樂道剛才的奇蹟。我則在下課後以跑百米的速度趕回家,迫不及待地向母親稟告這樁新鮮事。
當時飛越大溪的飛機很少,能夠看到飛機的機會一年沒有幾次,所以每次聽到飛機的聲音就會跑出屋外觀看,一直目送它消失於天際為止。如果碰巧在上課時聽到,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側頭往窗外看,根本沒有人聆聽老師的講課或寫字,於是老師便會暫停上課,准許我們跑到外面去觀賞。瞬間全校鬧哄哄的,所有班級的學生都爭先恐後跑到操場上,仰頭迎接飛機,一面鼓掌一面雀躍,大喊著:「飛機!飛機!」
當時的飛機是上下雙層機翼的小飛機,以單人駕駛居多,它的飛行高度不高,速度又慢,可以清楚的看到駕駛員。有一次,可能駕駛員看到我們在欣賞吧?特地繞回來從我們的頭上飛過,並揮手打招呼,我們興奮極了,齊聲歡呼:萬歲!萬歲!。那天晚上我竟夢見有兩架飛機降落於操場呢!像這種新鮮事層出不窮,隨著科技的進步,如電話、電影等新玩意,接連出現於故鄉讓我們驚訝不已。
雖然我生於貧家,住的是陋屋,穿的是粗衣,吃的是粗菜,但在雙親的慈愛及哥哥的友愛中長大,精神生活極為豐富。而且故鄉是貨真價實的山明水秀之世外桃源。映在眼簾的是一片綠油油的高山田野,溪水清澈見底,呼吸的空氣是甜的。與世風日下,自然環境日益污染的現在相比,有如天壤之別,當時好似活在天堂,令人永懷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