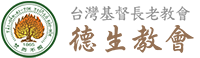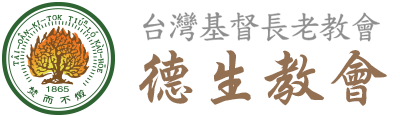家母於1894年(民前18年),出生在桃園縣大溪鎮的貧寒家庭,後來嫁給同樣是貧無立錐之地的家父為妻。家父是位樵夫,以做苦工所得的血汗錢來養育我們,母親則兼做些副業幫助家計。
因家父經年在深山裡伐木,回家和家人相聚的時間不多,家庭管理的重擔全落在家母肩上,她任勞任怨的與家父同甘共苦,建立了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
家母極重視教育,她本人雖然未曾學過日文,但上過私塾勤學中文,至今她朗讀「論語」的悅耳音韻,依然縈繞在我的耳邊,她一絲不苟抄寫「昔時賢文」的毛筆字跡也歷歷在目。她不但喜愛讀書,甚至加入吟詩會與同好文人互相研習作詩。當時(1920年代)的女人會讀書、寫字、作詩,可是一件足以轟動鄉里的奇聞,更何況她並非大家閨秀而只是一位工人的妻子呢!
家母對下一代抱了很大的期望,在節衣縮食之下、克服萬難安排我們兄弟接受良好教育,彰顯了無窮無盡的母愛。她不但重視學校教育,更重視家庭教育,以身作則教導我們如何去愛人、如何寬容別人、如何立身處世。使我最感動的家訓是:人的價值不在於你擁有多少錢財,而是你有沒有好品德,是否能夠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
她的教誨動人心弦,雖然她不是基督徒,但現在回想起來;她的教導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上帝的話。當時我們家雖然貧窮,卻充滿了愛及喜樂,精神生活極為豐富,看到了上帝的愛在我們裡面。
至1941年(民國30年),我和哥哥皆已就業,當雙親的重擔可由我們兄弟來分擔之際,卻爆發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和英、美等國啟開戰火,家兄被日軍徵召派往新幾內亞,擔任由台灣青年所組成的「勤勞奉仕隊」小隊長(排長)。而我也經武田藥品公司調派,前往印尼爪哇島,管理日軍由荷蘭人接收過來的奎寧農場。我們兄弟赴戰地前?後,家裡只剩一位年僅八歲的弟弟。這對父母親所帶來的精神壓力是難於以文字來形容的。
後來日軍節節敗退,雙親掛念我們的安危,寢食不安,日夜思念。這種憂懼對於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母親是致命的摧殘,後來得知;她憂慮過度失去了記憶,連親戚朋友都不認得,每天不斷地問起:「阿安(家兄)、阿福回來了沒?」,彷彿夢遊般地恍惚度日。
日本投降一年後被遣送回鄉,踏進家門遇到了久違四年的父親,他告訴我:你母親臥在病床,而且不認得任何人,恐怕連你也不認得。沒想到,走到臥房前就聽見母親說:「阿福的聲音!我聽見了!」進去房裡看見母親已站在床邊,一見面就開口說:「阿福真的回來了!」就伸手想要摸我。我衝上去緊緊抱住她,任由她撫摸我的頭臉,此時心裡悲喜交集激動得不能自持,痛哭一場。
之後,她寸步不離地跟著我,兩隻眼睛一直注視著我,好像一離開視線就會失掉我似的。從她充滿了慈憐的眼光,看到了真摰的母愛,深深體會到她無限的關懷和疼惜。
可惜我回家後不久,她因心臟病急速惡化,僅享年51歲就蒙主恩召,放下我們先回到天家。左鄰右舍異口同聲地安慰我說:「你媽終於等到你,安心地走了。」她一生勞碌,不求回報,付出一切心血教養我們,卻未留機會,讓我們好好報答她,令我至今仍深感遺憾。
懇求上帝垂憐,收留她在?的懷中,等我和她在天堂相見時,可向她稟告如何遵守她的教誨,建立了一個基督家庭,並努力以上帝的愛持家待人,盡心事奉主,讓她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