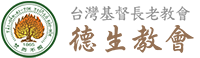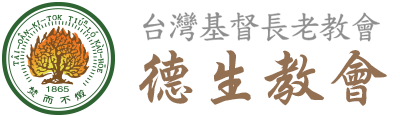民國 34 年,日本戰敗投降不久,戰勝國之美軍進駐爪哇,將所有的日本人,不管是軍人或是平民,一律收容於戰俘集中營。當時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仍屬於日本籍,而我碰巧僑居於爪哇,所以也被收容。當時我的心情極其複雜,思考著;我到底是戰敗國之日本國民,或是戰勝國之中國國民?如果是日本國民,罪有應得,被關是無話可說。但如果是中國國民,那應該還我自由之身才對,哪有盟軍把盟友關進戰俘營的道理?雖然滿心疑惑,仍不得不順從命運的安排,乖乖地被收容於四面圍著鐵絲網的集中營。
美軍對待戰俘非常仁慈,營內的一切行動也非常自由,不過時常被召去做工,搬運他們的補給物資。工作本身並不是怎麼粗重的,倒是精神上受的委屈比肉體上之痛苦更難受。美軍進駐萬隆不久,我們就開始被召。頭一次的徵召情形,雖然事隔六十多年,其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茲將當天的情形記載於下;當接到第一道徵工命令時,全營陷入一片恐慌與緊張之中。因為日本軍對待戰俘是非常無人道的,這可能是他們的「武士道精神」在作祟。他們認為,兩軍打仗時,士兵應該要戰到死為止,或是自盡,被敵方活捉是極大的恥辱,因此極為輕蔑俘虜,百般虐待他們。現在情勢逆轉了,戰俘們擔心美軍會以同樣的手段來報復。
此次被徵召的人數約五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出發前集合於廣場,聆聽指揮官的訓示,日軍爪哇區陸軍總司令寺田中將特地趕來慰勉,他擔心我們萬一受到美軍士兵的侮辱時,會以自殺來了結。因為日本軍人在戰敗後,都在絕望與沮喪中掙扎,而這次是美軍和日軍停戰後頭一次的接觸,他更擔心的是「士可殺,不可辱」的思想仍深植於日本軍人的心中,一時難改。
寺田中將訓示說:「天皇於停戰宣言中告誡我們要忍耐,無論碰到怎樣難受的事情也要忍耐,今天你們要為聯軍服務,不管遭受多大的侮辱也要逆來順受,千萬不可自暴自棄。日本是戰敗了,但必須復興,而復興的責任就落於你們這群年輕人的肩上,唯有活著才能擔得起復國的責任,如果死了,就沒有機會,那是不愛國的。所以你們要牢記;忍耐再忍耐,一定要活著回祖國 …」說到一半竟然哭起來,台下的隊員也感動的哭了起來,連我這位〝外國人〞也陪他們一起掉眼淚,深深體會到戰敗國的國民處境有多悲哀。
散會後我們分乘三輛卡車前往做工的地點…火車站。營外的世界與營內完全不同,映在我們眼簾的是自由繁華的景象,對被關在集中營的我們而言,這裡彷彿是天國。大家的心情也豁然開朗、即將剛才與司令官一起哭過的悲傷拋往天外,興奮地嘻嘻哈哈談笑著,好像要去郊遊似的。冷不防,飛來一塊石頭,「砰」的一聲打中了我們的車子,大家好奇的回頭一看;路邊站著一位年約十歲的金髮荷蘭小孩,舉起他的小拳頭,對著我們大罵「巴格野鹿!」。原來那塊石頭是他丟的。這也難怪、日軍的侵略,破盡了他們的養尊處優生活。看他那帶著稚氣的憤怒表情,讓大家驚醒了,重新纏清自己的身分。隨即陷入一片陰霾中。爾後至火車站的這段期間,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肯開口。
我們到達火車站時,美軍已在那兒。他們的人數約十人,互相行軍禮後,他們在我們面前操搶,填子彈,上剌刀,然後散開一列來監視我們。萬萬沒想到會在兵士監視下做工,其滋味又酸又澀,好難受。我們的工作是,將麵粉從火車上,搬上美軍貨車上,麵粉每包只有 22 公斤,所以每次都是揩兩包的,有一次不小心,將其中一包掉落於地上,這時的反應是:這一下慘了!!挨打!結果不但沒有,一位美兵,露出潔白牙齒笑一笑,把槍往地上隨便一擱,替我撿起那包麵粉。我們很勤快地工作,所以很快就完工,但這時大家大家都沾滿了麵粉,成為 ( 白人 ) 才結束了緊張的一天。
後來,台灣同胞得到日軍的資助,創立「台灣同鄉會」,另立門戶自行安排住食,眼見日本僑民陸續被遣送,同鄉會曾經推派代表前往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懇求蔣大使幫助遣返事宜,得到的回答竟是:「跟什麼人來,就跟什麼人回去!」,不但吝於伸出援手,反而破口痛罵:「你們做日本的走狗仔,有何臉來見我!」。
後來藉著日軍和美軍的協助返回台灣。在途中一直激動得不能自持,覺得前途一片迷惘。心想…日本曾以統治者的姿態蔑視台灣人,但戰後並沒有將我們丟棄,不僅完全負責被俘台胞的生活費用,在自身難保之狀況下,還負責把我們送回台灣;反觀衷心仰望的祖國,絲毫不關心我們的生死,反而被身為大使的官吏臭罵是日本的走狗。這對我們這一群滿腔渴望回歸祖國的熱血青年而言,無疑是迎頭被潑一盆冷水。不由不心中生疑…在集中營曾經每天認真學習中文,以生疏的國語互相練習會話,學唱國歌,暗誦國父遺囑,這一番認祖歸宗的熱情與期待,是不是我們自作多情的痴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