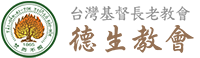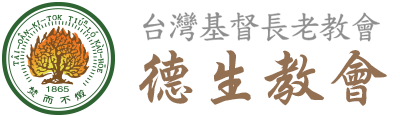我在家排行老三,又是個女娃兒,這尷尬的地位使我像夾心餅乾中間那一層,不被發現,難以看見。再加上出生在阿嬤家那個近二十人的大家族裡,阿嬤又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兒時的我,就像是個隱形人般無人理睬。
也許是害怕孤單更怕被遺忘吧!我因此發展出一個教人不注意也難的獨門絕技 — 哭。每個娃兒都愛哭,但是,我一哭起來便教人不敢領教。我的哭聲震天,我的肺活量十足,我可以哭上長長的幾個小時,令風雲變色,草木含悲;周旋反覆的哭聲,足以「繞樑三日,餘音不絕」。長大後,常聽母親提起:「妳一哭起來,連大人都想跪地求饒。」我早忘了自己究竟為何而哭,也不知是否想藉此引起別人注意。總之,大家都怕我哭,可是,他們愈是害怕,我愈是愛哭。孩子愛糖,更愛溫暖的哄抱,尤其在淚眼汪汪中,所有的安慰與關懷,更帶著朦朧之美,為我構築一個短暫的幸福世界。直到某次夜裡,我的哭鬧終於 換不到安撫,只換來冰冷的鞭痕和恐嚇的言語,我這獨門絕技才在江湖上銷聲匿跡。
那一天,母親關上了家裡的每一盞燈,我的世界陷入一片漆黑,家人一個個沉沉睡去,父親更是鼻息已雷鳴,睡不著的我忽然嚎啕大哭起來。靜謐的夜裡,連一根針掉落的聲音都清晰可聞,我那教人想跪地求饒的聲音在此刻更是響徹雲霄。爸爸媽媽被我吵醒,哥哥姊姊和弟弟也輾轉難眠,家中的燈又一盞一盞亮起。母親耐心地問我:「怎麼了?」我不答腔,只是用力、專心地哭,彷彿那一刻,我只為哭泣而存在。而一身疲累、睡眼惺忪,雙眼佈滿血絲,隔天還得早起上班的父親可沒像母親那般溫柔有耐性,他瞪大雙眼對我喝道:「不准哭!再哭!你還哭!」這一來,我哭得更大聲了。在驚恐中,我看著父親打開儲藏室的小門,用力抓起雞毛撢子,不由分說地往我身上猛打。頓時,我的哭聲轉成尖叫聲,我不顧一切,聲嘶力竭地哭叫著。挨打的疼痛似火,一道道地灼上我手我腿我身,還有,我的心上。父親見我哭鬧不休,又看見對面人家的燈也亮了,心裡又氣又急,於是,他像抓小貓一般抓起了我,跨著大步走向陽台,威脅著要將我丟下樓。母親見狀,嚇得趕忙上前制止,並柔聲勸我別再哭了:「別哭了!再哭,連小命都沒了!」我用盡全身力氣止住哭聲,終於,哭聲漸小,只剩下喘不過氣的抽噎,還有控制不住的顫抖,我的肩膀不住地抖動,我全身都發著抖。母親將我從父親的手中抱過去,邊安撫情緒激動的父親,邊關上燈,走進房間,放我在那張大床上,哄我睡覺。哭累了的我,不久便沉沉睡去。
隔天早晨醒來,我一睜開眼,便驚見深藍色的墊被上有根灰黑褐色相雜的雞毛在我身邊,還大剌剌地在我眼前顫動著,霸道地佔據我整個視野。那一刻,我開始心跳加速、口乾舌燥,剎那間,我的淚水又決堤了,哭聲幾乎要像山洪爆發般從我體內爆開來。可是,我定定地、害怕地望著那根羽毛,強自鎮定著,告訴自己:「不能哭,不能哭哇!」那根顏色暗沉的羽毛,留著昨天夜裡黑色的恐懼;那根輕飄飄的羽毛,藏著我沉重的心情;那根在空氣中微微晃動的羽毛,像在取笑我昨夜的抽噎與抖動。於是,我憋住哭聲,任全身發抖,任肩膀不住地上下顫動。
從此,雞毛成了比蟑螂、老鼠、毛毛蟲還要可怕的東西。在我眼中,雞毛撢子是來自黑暗世界的大魔頭,上頭那一根根雞毛,便是大魔頭手下的爪牙。而雞毛上灰白黑褐交雜的顏色,在我看來,既可憎又可怕,詭異又神秘,邪惡加討厭。就連菜市場雞肉攤旁的那一籠雞,都令我心生恐懼。
從四歲至今,我的「雞毛情結」不曾稍離,甚至有增無減。於我而言,雞毛是這世上最可怕最惹人厭的東西。偶爾看到有人用雞毛撢子撢車,或是看到路上有人載著大大小小的桶子和清潔用具,行李架上還綁著雞毛撢子,我一定敬而遠之,繞道而行,深怕一陣風吹來,那可怕的雞毛會順勢飛上我身,撲上我的臉 …… 這、這、這 …… 簡直是要人命的恐怖事件,足以引發一連串的慘劇 — 發抖、尖叫、手腳發軟、臉色發白、摔車、昏倒,並且希望自己永遠不要醒來,永遠離開這個有雞毛的世界,直到那超級恐怖的東西消失在這世上。
若真有那麼一天,我希望這世上有人能用輕吻喚醒我,告訴我:「香瑩,醒來吧!看看這美麗新世界 — 一個沒有雞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