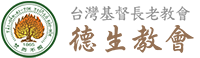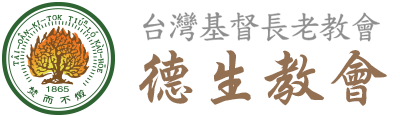母親節徵文比賽青年組第一名
走出紀錄片放映室,臉上的兩行淚水初乾,在午後的春風裡,聞到的是母親的愛。
永遠記得那年的女性影展,只不過是買了套票來打發一個下午的時間,一部跟紅斑性狼瘡有關的紀錄片,翻動著我對母親深層的感激與心疼。
我跟曾經也患疾的紀錄片導演說,「謝謝妳拍這部片……」導演或許不知,在幽暗的放映室裡,那些疾病中所有的慌亂、焦慮與痛苦呈現在眼前,我也才知道原來母親在許多年前,在我如今接受醫學訓練的好多年前,是如此靜默地咬牙撐過死蔭的幽谷。
在大學幾年間,接觸了許多有關女性的思潮。這些思想的啟蒙,常常讓我不斷的翻閱往事,在許多生命中出現的女性的閱歷當中,試圖檢驗著這些所謂女性主義,所謂解放,所謂自由的突破、衝撞。借著文字、影像,來對照現實中女性的角色。我常以為這是一種具備智慧與氣魄的關懷。
仍記得國中時在母親的書架上取下一本《內在革命》,後來我也才知道那是本美國女性主義的經典啟蒙。
還有最近一部描述女性主義作家吳爾芙的生命的電影《時時刻刻》,讓曾經一同「研究女性」的朋友仍趨之若鶩。在偌大而空曠的電影院中,片尾女主角走入河裡犧牲而深沈哀愁的片尾音樂響起時,我仍想起了母親。
許多的閱讀與論述,讓我瞭解對一個想要在傳統價值中突圍的女人,是多麼被困擾在自由與順服當中。而母親呢?如果媽也曾經那樣閱讀著解放的經典,那這些年來守著她「家後」的角色,像歌手江蕙淒美的歌聲娓娓道出的「阮將一生嫁互恁兜」,到底對媽而言是否真的是心甘情願?雖無法猜測其中可有怨悔,但她每天忙碌地一面為父親的診所忙進忙出,又得為孩子們的種種操心,幾乎看不出有哪些時間撥給了她自己。
許多年前,我們也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準備到加拿大開啟嶄新的生活。當時讀國中的我和雙生兄弟,天真的以為這麼做就能擺脫台灣的聯考,到異國去經驗活潑的教育。媽為了我們,顧不得自己因更久以前留下的眼疾去學開車、練打字。我們都不知道這些付出,媽背地裡忍著的是她的宿疾帶來的關節疼痛的折磨。
後來移民計畫仍因媽的身體狀況止步。我們三兄妹的戰場轉移到台灣本島,媽陪我們在台中讀書,她的紅斑性狼瘡又再發作了。
目睹母親每天必須承受化學治療帶來的苦楚;在暗夜裡依稀聽見廁所傳來的嘔吐聲,浴室裡那些一大撮一大撮輕輕即能扯落的頭髮,以及服用類固醇而浮腫的臉頰。當時候的我們,比起讀小學時母親第一次發病,更深知她承受的痛苦之劇。
然而媽卻只要我們專心讀書。她撐著虛弱的身體,仍每天打理家務,為我們準備豐盛的食補,如今想來,才驚覺自己過往的自私。三年高中的聯考之役打得漫長,而戰情才稍微明朗,我又不知足地重考去了。緊接著的又是母親四處為休學奔波,那樣幾近捨命之恩,卻是我在遙遠的北部都會所一度忽視的。
一直到媽發病很久以後,我們才曉得,她是因為在與鄰居爭地而成受不起過大的壓力而病倒的。當年媽為了爭取房子後面的一小塊地,以為將它闢成後院,也能增加我們孩子房間窗外的空間。沒想到這樣的堅持,竟是帶給母親苦難的開始。
而其實早在更久以前,媽剛嫁來婆家時,早常因為許多壓力而飽受身心的煎熬。從她回憶懷孕時暈倒在市場這段怵目驚心的故事,依稀能描繪她從孩子尚未出世就開場的受難史。
在剛上大學之前,對母親的印象,就是那般憂鬱而柔弱。我雖知疾病從她身上奪去了太多,卻仍自怨自艾地喟嘆自己的不得志,因此看見的只以自己為中心的生命。直到上大學以後,另一個轉捩點,解開了許多的情緒與未解的生命繁結。
那是讀大一時,五月的事。在陰雨濛濛中,接獲媽用中文傳呼傳來的幾個至今永難忘記的字–「爺爺病危,請快回家」。當年我在高速公路上以一百二的時速飛奔回家。而那晚,祖父過世了。
只是短短的一天,祖父的過世成就了我們一家的重大轉變,也是祝福。祖父的臨終受洗,而使得家人尾隨祖父,一一進入基督的懷抱。關鍵在於媽在祖父受洗前的一句鼓勵。她的一句:「沒要緊,咱以後攏作夥。」讓祖父心甘情願地接納他一生從未相信的基督。
媽是我們家最積極追求信仰的人。那彷彿是一種命定,標記著對宗教信仰的義無反顧。從過去帶著孩子們到廟中祭拜,或隻身到佛光山上點燈,或追求藏密佛教。
然而曾經告誡我們若信基督她就「沒人拜」的母親,卻在幾年前隨著祖父的過世,也夥同父親受洗了。教會的牧長到家中舉行聖別禮拜當天,母親在佛堂裡痛哭。後來問起,才知道她與外婆相約來世再做母女的承諾將要終結。
和許多初信基督的人的喜樂相比,母親的哀哭,似乎顯得格格不入。我與弟弟在父母受洗後隔年也領洗,當時也正植信仰的「蜜月期」,在大學團契裡服事、讀經,過著充實的信仰生活。當時讓我心心懸念的,是對家人的信仰根基的質疑。我害怕父母沒有讀經、沒有團契生活。
但自從有天我從南台灣回到彰化家中,在午夜時分仍期待與父母分享時,我看到爸媽一起坐在床上俯首禱告。那是一段又靜又長的片刻;是充滿了對自己信心的懊悔與對上帝的感動的片刻。
往後幾年間,我看見爸媽積極的參與教會聖歌隊、團契、查經班,以及各樣服事。媽常常負責教會禮拜堂的插花。其實她也成在家中布置許多插花的盆栽,並三不五時要問我們一句「好不好看?」缺乏審美能力的我總是三兩句地敷衍,但如今我卻在那一盆盆的花卉中,看到母親因著上帝而來的活力朝氣。
如今,家中的學生都上大學了。母親再也不是我們中學時代時陪著我們經歷時時刻刻的酸甜苦辣的角色。我們讀大學的三兄妹,分散在台灣的北中南三地。偶爾我們還會出國旅行,而媽只能藉著電話關心。
忙碌的大學生活使得媽終於不得不抱怨,孩子們只把家當作「旅舍」般地回來匆匆離去也匆匆。雖然她現在無法心血來潮時就端出一盤麵線還是一鍋魚湯,但也總在我們三過家門終於肯探進「旅社」時,抓住機會塞入幾罐維他命還是蜂膠。或許終究要等到為人父母的一天,才能體會母親的牽掛罷。
近日我開始以網路的及時視訊會議和深處異地的弟妹聊天,這招被媽瞧見,她也「新欣」(台語)地要求我們幫她架設網路視訊設備。常常在與母親身隔幾百公里之遙的夜裡,仍聽見媽因為透過網路見到我們的面容而興奮地大笑。我很高興我們能用這麼「娛樂」的方式來轉化這種牽掛。
如今媽很前衛地用電腦麥克風,叮嚀著在醫院見習實習的我們要多洗手、多保重,免得感染流行一時的肺炎。當然,也常常多加了以往沒有的勸勉:「要多讀聖經喔!」
年初我們一家在餐桌上分享一年來最感恩的事情。媽說她很感恩有機會參與教會的查經班,有機會領受上帝的話。媽終於可以不再因為而女兒每天操心,卻也不忘記將自己的收穫分享給家人。
想起多年前在母親的床頭翻到的,那本在我和弟弟都還很小的時候寫下的「育兒日記」,就知道在我們還未學會說話時,媽已經開始用日記寫下心情,一點一滴。「今天你們又把為衛生紙拿出來玩囉……」
原來從一開始,媽的心思意念,沒有一刻從我們身上移開。就這樣牽掛著,無論身體好壞、心情好壞,無論在醒著、夢裡……
看著母親從生病到好轉、從焦慮到平安、從奄奄一息到活力四射,除了知道母親靠著意志力而堅守母親的角色,也深知信仰帶給她的醫治力量之大。
年初在團圓飯中,家人分享了各自最感恩的事情。媽說他最高興的是參加教會查經班,有機會認識上帝的智慧與訓勉,帶給她無比的充實與喜樂。回想她的基督信仰歷程,雖沒有初信時的甜甜蜜蜜,卻有倒吃甘蔗的美麗境界。
如今我們幾個做孩子的,像翅膀初硬的雛鳥,正懵懂卻也自以為是地到處遨翔。尤其上了大學,有時我們會很義憤填膺地表達許多意見,但媽的答案總是永遠單純而鏗鏘有力:「禱告吧!」
媽知道她終於管不動我們了。但與我們做孩子的關係,竟越來越像可以互相交心的親密朋友。我們看著她在上帝的愛裡越來越年輕亮麗,幾乎看不出曾得過重症。而她在我們作孩子的越來越能獨立之時,終於有了更多自己的時間,可以與朋友組讀書會、學插花、參與團契、聖歌隊、查經班……簡直不輸多采多姿的的學生生活。
又將逢母親節,我仍不免俗的到百貨公司一晃,看看有什麼可以做為禮物。然而置身百貨公司,卻也令我想起妹妹曾經對我說的,她多麼喜歡逛百貨,因為從小時候起,每當妹妹心情不好時,百貨公司就變成媽和妹妹的交心之地。吸引她逛百貨的不是玲瑯的商品,而是母親深沈的愛的記憶。
母親的愛就像一條靜靜的寬闊的長河,不吭一聲,靜靜地流。她知道何處該轉彎,因此也從不激越澎湃,但卻在河道深深割出廣納著包容與關懷的河床。她時時刻刻包容一切的無奈與恐懼,包容傳統角色的束縛和疾病的折磨,在面對死亡關頭時卻忍著恐懼。
於是這條愛的長河,匯集了所有的疼痛與無奈,一起帶到信仰的海洋。這一路上灌溉孕育著的,是家庭,是她對我們作孩子們的,也是對父親的,永遠深刻的關心的體現。這也是我在許久以後才明白的,所謂最激進的社會關懷,其實是家庭的實踐–媽是我心目中,最典型,最動人的模範。